音樂並非為人娛樂所用,而是用以通神明,和天地,正人心。
南方的天氣悶熱潮濕,灰濛濛的空氣讓人感到壓抑、煩悶。連日來為研究院音樂療法的用曲而傷腦筋,至今尚未有頭緒。我望著窗外,見天色尚早,順手拿起床頭上未看完的書看了起來。漸漸地被書中“鄒衍吹律”的故事所吸引。
鄒衍,是戰國末期稷下學宮的著名學者、陰陽家的代表、五行學說中五德終始說的創始人。因他通曉陰陽五行,喜歡談論天地運行的規律,是大德高士,當時人們稱他“談天衍”,又稱鄒子。傳說鄒衍到燕國時燕昭王親自為他執帚掃階。當時的漁陽郡也就是現在的北京密雲地區,氣候十分寒冷,五穀不生。一天,鄒衍來到漁陽的一個山谷,看到已經是春天了,但穀內卻是一片寒冬的景象,百姓生活十分饑苦。他拿起隨身的律管,坐在山上吹起了春之曲。鄒衍吹了三天三夜,穀內吹來暖風,冰雪開始消融,氣溫變暖,草綠花開。從此,漁陽的氣候變得溫暖,黍穀可在此寒穀內生長。為了紀念鄒衍,老百姓把此山叫做黍穀山,山中建有鄒衍祠,祠前的銀杏樹歷經二千多年至今仍在。李白曾寫《鄒衍穀》:“燕穀無暖氣,窮岩閉嚴陰。鄒子一吹律,能回天地心。”

我不由地對鄒子心生敬意。十分好奇他的樂曲為何能有如此神力,對那出神入化的樂曲產生無限地嚮往……
朦朧中一陣悅耳的鈴聲傳來,耳邊響起了樂聲,鄒衍先生緩步向我走來,我趕忙起身,恭敬行禮。
先生似乎看穿了我心中的疑問,說:“你可想知道我的樂聲為何能引來春氣使寒穀春暖花開?”
我答道:“是。先生是如何做到的?”
鄒子說:“音樂並非為人娛樂所用,而是用以通神明,和天地,正人心。黃帝令伶倫截竹為管,候氣定律。所創作的《清角》能夠溝通天地,號令鬼神。舜帝的《大韶》樂舞奏畢,有丹鳳來儀、百獸起舞。孔子曾贊《大韶》之樂盡善盡美。聖人之樂能平衡陰陽,疏通引導萬物,使自然回歸和諧狀態;君子奉行其道,修心養性,安身立命。遠古朱襄氏為帝時,怪風四起,陽有餘而陰不足,各種作物枯死,盛夏時節還流行瘟疫,民不聊生。朱襄氏造五弦瑟,演奏《來陰》之曲。引來陰風,使陰陽二氣平衡,萬物生而萬民安。我只是遵循了聖人之道,故樂聲能引春氣入寒穀。”

我施禮道:“願聞其詳。”
鄒子說:“先聖們所創的樂曲都是效法自然、對應天道運行規律的。大雅之音與五行相順,與天地相和,與神明相感。五音與五行、五臟相對應,十二律與十二地支、十二月、十二時、人體的十二經相對應。世間萬物莫不與陰陽五行相合,若能掌握陰陽五行之道,謹守五德,就能精神平和,衰氣不入,天地交泰,遠物來集。”
我歎道:“恨我生不逢時。如今大樂已失,再無福領略如此妙音了。現代的人多災多病,不如意事常八九,人心恰如昔日寒穀。”
鄒子笑道:“天道何曾有失!”
我心中一震,正若有所思間,伴著“隆隆”的雷聲外面淅淅瀝瀝下起雨來。我一怔,思想回到現實中。推開窗,一陣清風吹過,帶走了多日的煩悶。
是啊,天道何曾有失。老子論道“獨立不改,周行而不殆”。古人效仿自然規律奏出的樂曲可與宇宙萬物產生共鳴。老子說:“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”。黃帝的《雲門》、堯帝的《大鹹》、舜帝的《大韶》、大禹的《大夏》、商湯的《大濩》、武王的《大武》,六代之樂都是用來祭祀天地、山川和祖宗的,表達了古人對自然環境的敬畏和對先祖的崇敬。
天人相應,音樂同樣可以與人體產生共鳴,從而動盪血脈、通流精神、和正人心,會產生不可思議的效果。《呂氏春秋·適音》闡述了音樂是為了使人心平和的,人心平和而使人行為舉止得當。《禮記》有“古之君子必佩玉。右徵角,左宮羽。”、“君子無故,玉不去身”之說。是說君子的行走坐臥必須進退有度,玉佩就會隨之發出和諧的樂聲;君子的車上掛有鑾鈴,乘車出行時鑾鈴相和發出悅耳的奏鳴聲。這樣君子可時時提醒自己正心誠意,規範自己的思想和行為,因而使邪不入侵。
我頓時豁然開朗,點燃一支檀香,正襟危坐。漸漸地,周圍一片寂靜,只有我細微的呼吸聲在空中飄散……。我的思想走進了森林,流水、鳥鳴、微風吹過樹梢的沙沙聲,我陶醉其中,享受著這天籟之音。
忽然,我有了靈感,趕忙打開電腦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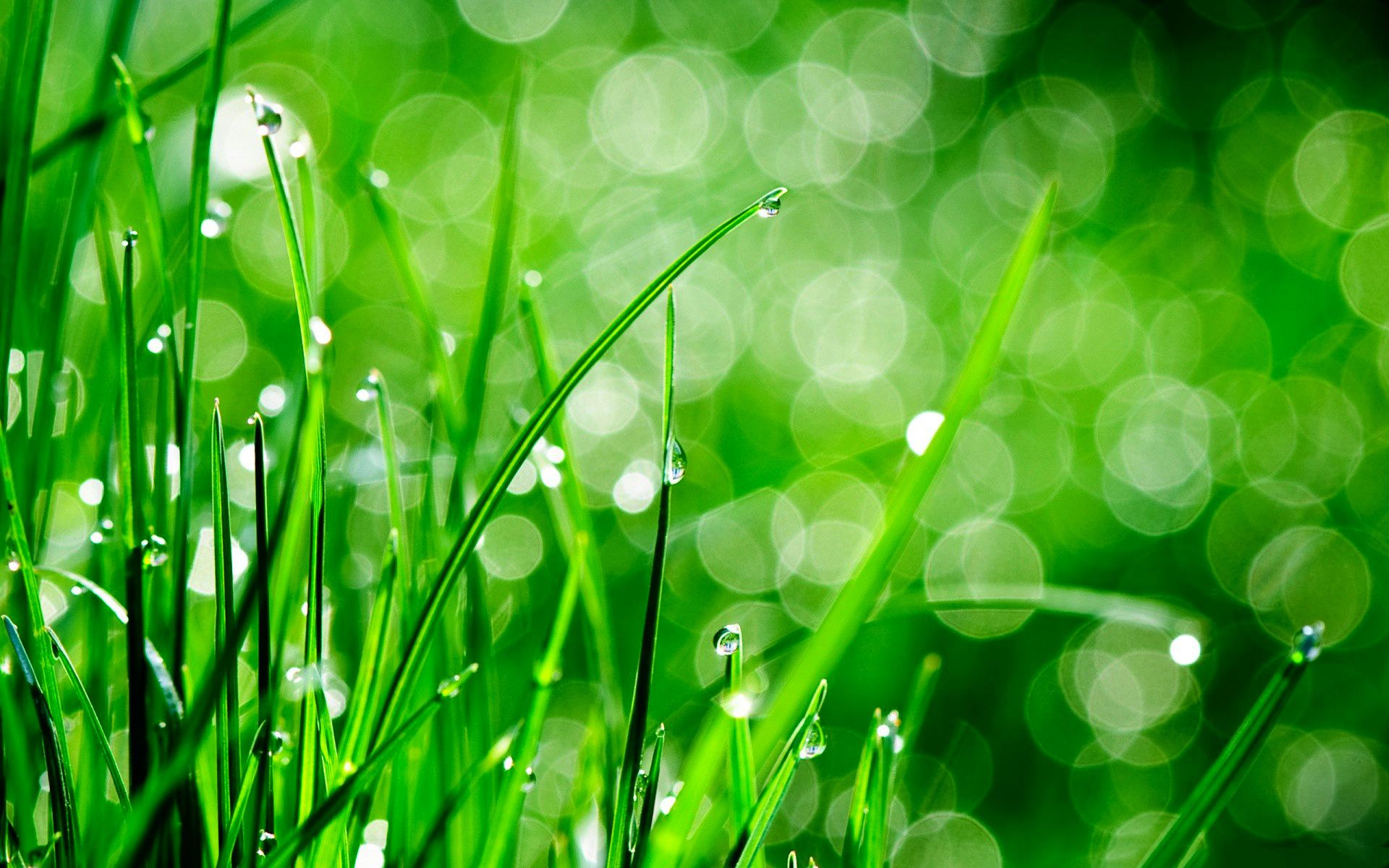
終於把音樂療法的用曲完成了。我起身來到窗前,雨不知什麼時候停了,太陽出來了,風卷著的紫荊花瓣漫天飛舞,落在窗外的草地上。經過雨水洗刷過的草兒顯得格外的綠,掛滿了水珠,在陽光下熠熠生輝。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