音乐并非为人娱乐所用,而是用以通神明,和天地,正人心。
南方的天气闷热潮湿,灰蒙蒙的空气让人感到压抑、烦闷。连日来为研究院音乐疗法的用曲而伤脑筋,至今尚未有头绪。我望着窗外,见天色尚早,顺手拿起床头上未看完的书看了起来。渐渐地被书中“邹衍吹律”的故事所吸引。
邹衍,是战国末期稷下学宫的著名学者、阴阳家的代表、五行学说中五德终始说的创始人。因他通晓阴阳五行,喜欢谈论天地运行的规律,是大德高士,当时人们称他“谈天衍”,又称邹子。传说邹衍到燕国时燕昭王亲自为他执帚扫阶。当时的渔阳郡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密云地区,气候十分寒冷,五谷不生。一天,邹衍来到渔阳的一个山谷,看到已经是春天了,但谷内却是一片寒冬的景象,百姓生活十分饥苦。他拿起随身的律管,坐在山上吹起了春之曲。邹衍吹了三天三夜,谷内吹来暖风,冰雪开始消融,气温变暖,草绿花开。从此,渔阳的气候变得温暖,黍谷可在此寒谷内生长。为了纪念邹衍,老百姓把此山叫做黍谷山,山中建有邹衍祠,祠前的银杏树历经二千多年至今仍在。李白曾写《邹衍谷》:“燕谷无暖气,穷岩闭严阴。邹子一吹律,能回天地心。”

我不由地对邹子心生敬意。十分好奇他的乐曲为何能有如此神力,对那出神入化的乐曲产生无限地向往……
朦胧中一阵悦耳的铃声传来,耳边响起了乐声,邹衍先生缓步向我走来,我赶忙起身,恭敬行礼。
先生似乎看穿了我心中的疑问,说:“你可想知道我的乐声为何能引来春气使寒谷春暖花开?”
我答道:“是。先生是如何做到的?”
邹子说:“音乐并非为人娱乐所用,而是用以通神明,和天地,正人心。黄帝令伶伦截竹为管,候气定律。所创作的《清角》能够沟通天地,号令鬼神。舜帝的《大韶》乐舞奏毕,有丹凤来仪、百兽起舞。孔子曾赞《大韶》之乐尽善尽美。圣人之乐能平衡阴阳,疏通引导万物,使自然回归和谐状态;君子奉行其道,修心养性,安身立命。远古朱襄氏为帝时,怪风四起,阳有余而阴不足,各种作物枯死,盛夏时节还流行瘟疫,民不聊生。朱襄氏造五弦瑟,演奏《来阴》之曲。引来阴风,使阴阳二气平衡,万物生而万民安。我只是遵循了圣人之道,故乐声能引春气入寒谷。”

我施礼道:“愿闻其详。”
邹子说:“先圣们所创的乐曲都是效法自然、对应天道运行规律的。大雅之音与五行相顺,与天地相和,与神明相感。五音与五行、五脏相对应,十二律与十二地支、十二月、十二时、人体的十二经相对应。世间万物莫不与阴阳五行相合,若能掌握阴阳五行之道,谨守五德,就能精神平和,衰气不入,天地交泰,远物来集。”
我叹道:“恨我生不逢时。如今大乐已失,再无福领略如此妙音了。现代的人多灾多病,不如意事常八九,人心恰如昔日寒谷。”
邹子笑道:“天道何曾有失!”
我心中一震,正若有所思间,伴着“隆隆”的雷声外面淅淅沥沥下起雨来。我一怔,思想回到现实中。推开窗,一阵清风吹过,带走了多日的烦闷。
是啊,天道何曾有失。老子论道“独立不改,周行而不殆”。古人效仿自然规律奏出的乐曲可与宇宙万物产生共鸣。老子说:“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”。黄帝的《云门》、尧帝的《大咸》、舜帝的《大韶》、大禹的《大夏》、商汤的《大濩》、武王的《大武》,六代之乐都是用来祭祀天地、山川和祖宗的,表达了古人对自然环境的敬畏和对先祖的崇敬。
天人相应,音乐同样可以与人体产生共鸣,从而动荡血脉、通流精神、和正人心,会产生不可思议的效果。《吕氏春秋·适音》阐述了音乐是为了使人心平和的,人心平和而使人行为举止得当。《礼记》有“古之君子必佩玉。右徵角,左宫羽。”、“君子无故,玉不去身”之说。是说君子的行走坐卧必须进退有度,玉佩就会随之发出和谐的乐声;君子的车上挂有銮铃,乘车出行时銮铃相和发出悦耳的奏鸣声。这样君子可时时提醒自己正心诚意,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,因而使邪不入侵。
我顿时豁然开朗,点燃一支檀香,正襟危坐。渐渐地,周围一片寂静,只有我细微的呼吸声在空中飘散……。我的思想走进了森林,流水、鸟鸣、微风吹过树梢的沙沙声,我陶醉其中,享受着这天籁之音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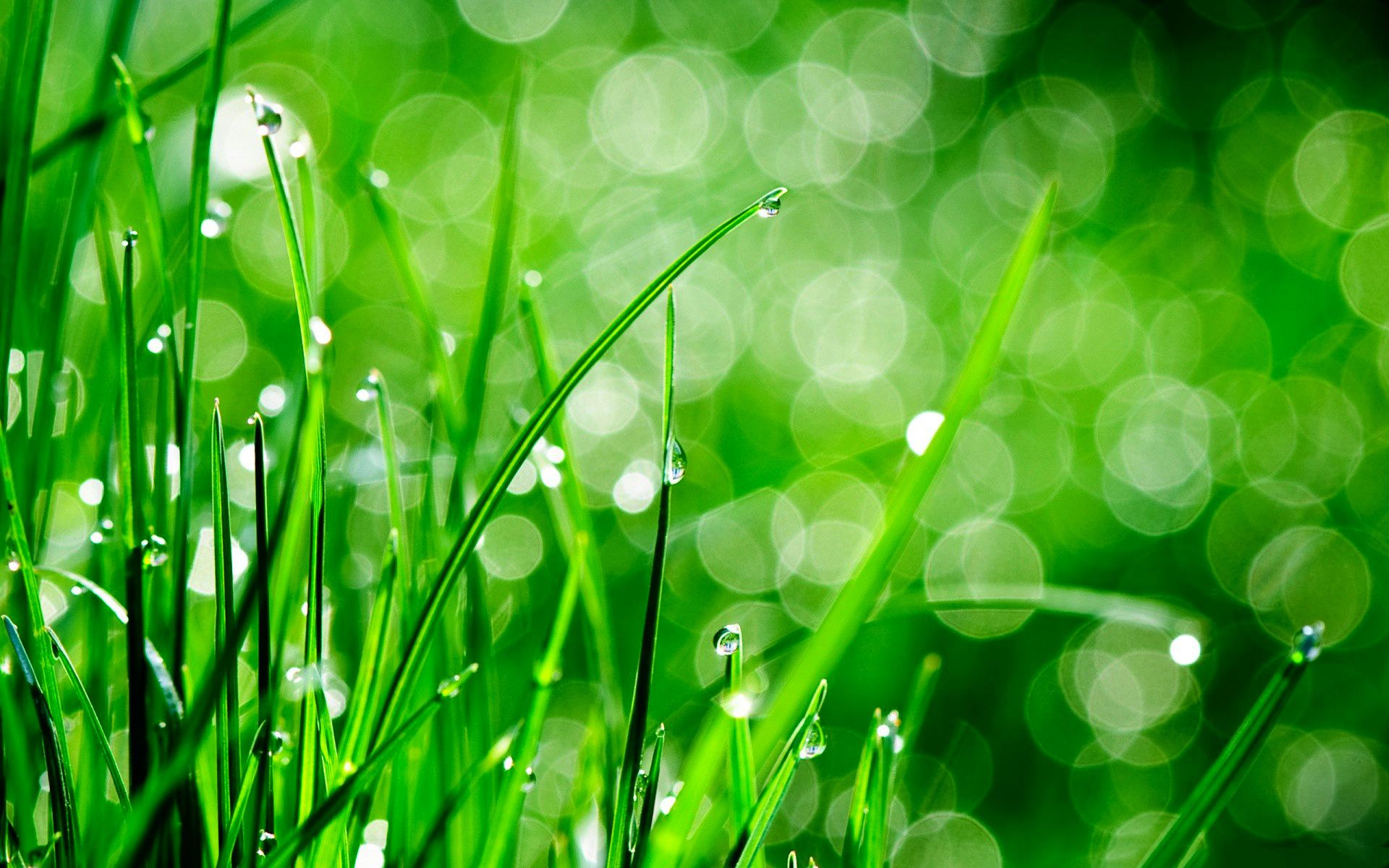
忽然,我有了灵感,赶忙打开电脑。
终于把音乐疗法的用曲完成了。我起身来到窗前,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,太阳出来了,风卷着的紫荆花瓣漫天飞舞,落在窗外的草地上。经过雨水洗刷过的草儿显得格外的绿,挂满了水珠,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


